☆、无条件的一代(上)(4 / 4)
约格尔在巴黎与政要往来时,我受命处决一批战俘。他们已经被解除武装,手无寸铁,我第一次感到一丝罪恶。换一种角度呢?我杀掉的法国士兵脱下军装,也是个普通人,他的家可能就在里昂的某个宁静村庄,家人在满怀希望的等着他回家。我杀掉的是一个儿子,或许还是一个父亲,一个丈夫。
我是个杀人犯,军装为我的行为提供了正义而铁血的借口。这是战争侵蚀心智的另一种方式,它让我们变得过度冷血,又过度愧疚。帝国一路从高歌猛进,到保守应战,再到大厦将倾,直至最后穷途末路,六年战争,大小数十场战役,这是我全部的服役生涯。我们举枪,前进,时刻准备战斗至死。我期盼却又不敢奢望能和朋友像以前一样坐在一起,尼克劳斯的战场在深海,他与我太远,而约格尔,他的变化太快,让我们措手不及。
在我们分别之前,我曾问他,对战争没有没畏惧。约格尔回答:我们才是主宰者,整个欧洲都将战栗着匍匐在我们脚下。
我想,他爱上了这场战争。
约格尔以前绝不是这样,他的严肃认真最讨学校的教官的喜爱。考入军校之前,我们四个人间的玩闹与其他普通朋友没有不同,当年我与他们一同翻墙出去参加酒馆舞会,第二天东窗事发被按在教室写检讨。去年我听闻几名犹太人翻越高墙逃出隔离区,约格尔对他们下了杀手。战争对他的影响出乎意料,他把曾在艺术上无与伦比的创造力和想象力用在谋害性命上。以前,他对世界上所有的颜色都感到愉悦,现在只剩下血红能带给他一点生气。
如果没有这该死的战争,谁说约格尔不会是本世纪最炙手可热,最具创造力的德国画家呢?至于我,也许父亲不会再执着于让我参军入伍,那么我会进入乐队,去世界巡演。
如果没有战争,娴该成为一名钢琴家的夫人,而不是一个纳粹战犯的妻子。
相关小说
- 冷宫奴妃
- 17K小说网VIP2013-08-09完结 他恨她,奉皇命杀她全家,将她失语弟弟双腿打断,把她变成河蟹欲望的禁脔,挥鞭无情,夜夜强索。 她恨他,她杀他妃嫔,助他敌对,举剑布棋处处紧逼,翘着小指巧笑嫣然的为他倒上了一杯醇香的毒酒。 她沐水重生,周旋在后宫之中步步为营...
- 07-05
- 再世权臣
- 【再世权臣大陆商志即将上市,出版名《海晏河清》,正在全网预售中,书店链接见围脖 @天天天谢】 一朝身死,苏晏穿成了个古代文弱书生,走上被众攻环绕的权臣之路。 笔笔皆情债,步步修罗场。 枕万里河山,享无边风月。 【架空背景,有参考朝代,但谢绝考...
- 12-11
- 愿以山河聘
- 【本文已签简体出版,具体可关注微博,原名《嫁给暴君后我每天都想守寡》,封面来源于广播剧海报】 下本《和邪神结婚后》已开。 【本文文案】 秦王姬越是令七国闻风丧胆的暴君,却有这么一个人,风姿羸弱,面容楚楚,偏敢在他面前作威作福。 年轻的帝王沉...
- 03-27
- 伪装学渣
- 【入V通知:本文将于1.19日周五入V,感谢各位大佬支持,啾!——来自你们短小的陷入万字大更深渊的眉头一皱黄九】 分班后,两位风靡校园的“问题少年”不止分进一个班还成为同桌。 明明是学霸却要装学渣,浑身都是戏,在表演的道路上越走越远。 -818我们班里...
- 05-04
- 楚囚
- 长佩2019-6-16完结 文案:狗血低俗。 生子 傻/黄/不太甜 有十年,何楚是由墓碑,不眠夜,还有苦涩的回忆组成的。 他想以后都会好的。
- 03-11
- 男配破产后[穿书]
- 文案 一朝穿越成破产男配, 水电费交不起,全网黑找不到工作,陈盏决定……先来一本自传发家致富。 回忆恶毒男配生平,写下人生三部曲《忏悔录:叛逆少年情感的萌芽与堕落》,《我迫害影后的那些年》,《以卵击石:仇富让我对豪门总裁屡次诋毁》…… 其中《忏悔录...
- 05-31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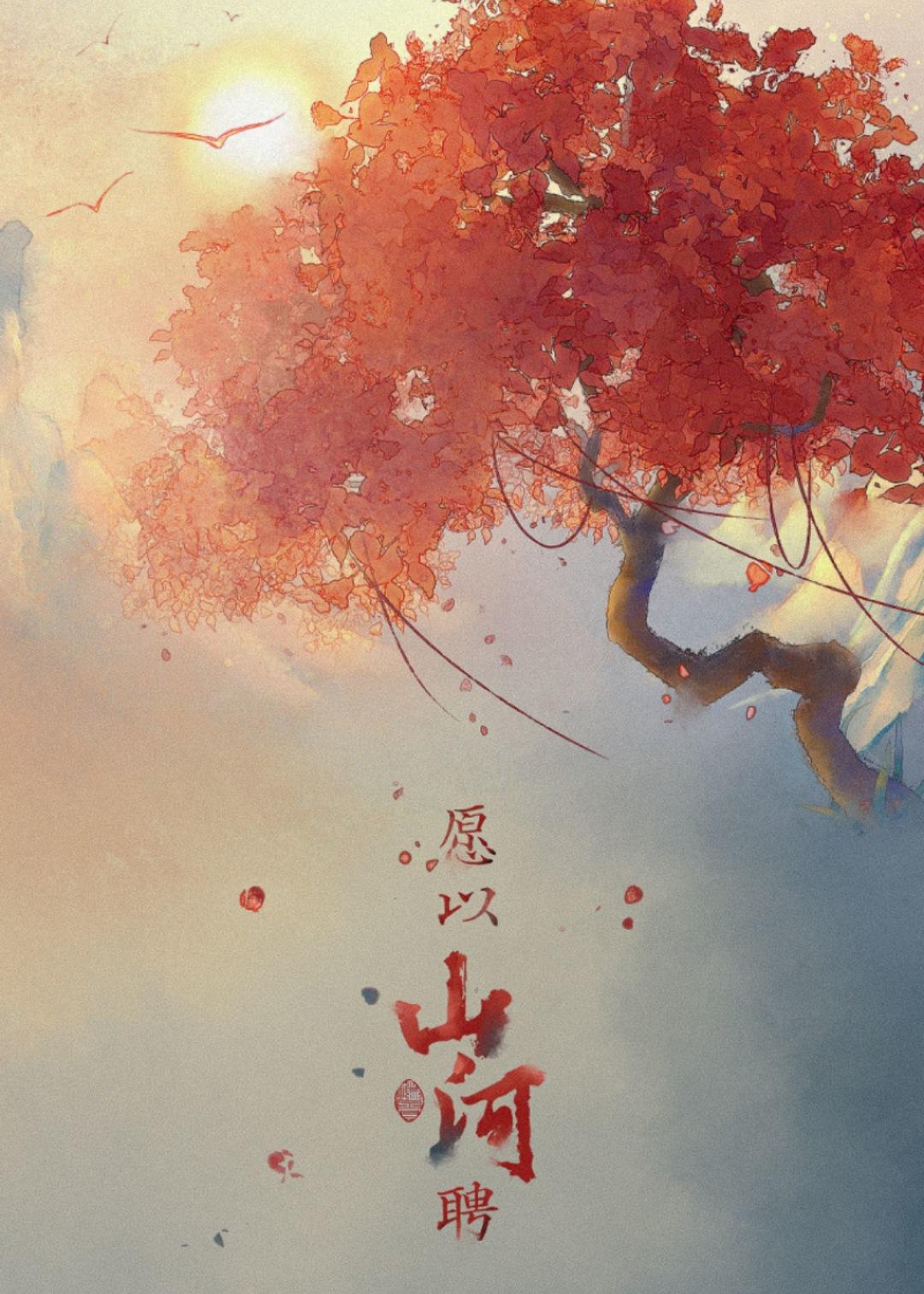


![男配破产后[穿书]](https://www.aqxs1.com/files/article/image/13/13496/13496s.jpg)